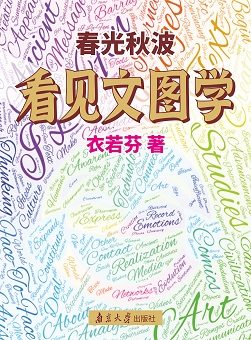2024年2月5日邱誌勇教授(台湾清华大学)
“虚拟作为一种扩延的新真实”讲座纪要
撰文: 邓雅文
引言介绍
“虚拟作为一种扩延的新真实The Virtual: An Extension of New Reality”的主题讲座于2024年2月5日晚上7点至8点半线上进行,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衣若芬教授主持、国立清华大学艺术学院邱志勇教授主讲:
虚拟实境(VR)是近年来最新的文化科技潮流之一,许多文化活动或人际关系开始以虚拟的方式进行,学者将此文化现象称之为「虚拟转向」,更关注虚拟转向在艺术领域中的美学哲学意涵。尽管关于虚拟实境的哲学研究与论述已相当多,但是却始终未获得美学家的关注。因此,本演讲试图将虚拟实境视为一种媒材/体(如同绘画、电影、摄影般),讨论其衍生出的新真实,及其想像空间的配制方法,借以宣称虚拟媒介与哲学美学间所密切的连结更在彰显于虚拟媒介与感觉、知觉的关联性,强调在虚拟媒介中的平凡感觉与知觉能力也是一种真实,让人们得以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知觉能力。(讲座简介,邱志勇 2024)
邱志勇教授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大学跨科际艺术系博士,双主修视觉艺术与电影,副修美学。学术专长为数位美学、科技文化研究、艺术评论与策展。邱教授现为国立清华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科技艺术研究所教授暨所长、艺术学院学士班主任,同时为策展人、艺评家与影像创作者、财团法人数位艺术基金会董事、文化研究学会理事。
主要内容
讲座首先简要概述了从20世纪6、70年代开始“虚拟”就不断的在被实验成为一种新的可能性。到了90年代,有观点认为“虚拟”是跟“真实”完全对立的一个状态。一直到2016年被称之为是VR元年之后,大家对 “虚拟”跟“真实”之间的一种二元对立的看法,又产生了不同的论述思路。当代尤其在2020年之后,可以看到一些哲学、理论、文化研究相关的论述中,都不断在谈到“虚拟”是有可能成为一种人们重新去认识“真实”/“现实”的一种新的媒体。
邱教授也由此角度深入切入,运用西方哲学范式中的理论观点,以佐证“虚拟作为一种扩展的新现实”的论点。借鉴David Chalmers在《Reality Plus》中的观点,Chalmers重新界定了“虚拟”概念,将其视为新型物质文明的一种主张,从而突显出当代视觉中心主义的新型观察状态,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来感知世界。在此背景下,探讨了虚拟技术如何融入到其他物质、影像,甚至全新的文化结构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理解这些通过技术所产生的影像、图像、文字等表现形式。
在12至13世纪的中世纪时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新建的教堂呈现出一项重要的艺术特征,即彩色玻璃。这些玻璃通过视觉化手法将圣经中的文字描述转化为图像装饰,并借助日光透过玻璃的效果产生多彩光影,从而创造了一种视觉上的虚拟体验。这个过程本质上构成了一种“虚拟”界面,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如小礼拜堂,让信徒在心灵层面与上帝进行沟通。直至巴洛克时期,这种虚拟体验仍然通过建筑内部的穹顶绘画得以延续。通过开放式构图的形式,这些绘画打破了结构上的限制,使建筑内的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种想象的场景中,可以直接与所谓的天堂进行交流。所谓的“虚拟”体验主要停留在心灵交流和想象的层面。
1935年,Weinbaum在其文学作品《Pygmalion’s Spectacles》中描绘了一种虚拟现实体验,即主角戴上一副眼镜后能够置身于一个模拟的环境中,该环境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以及触觉等多个感官的体验。这种通过视觉刺激为主的影像结合先进科技设备,实现了一种延伸并加强感知体验的沉浸式技术。这种概念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超前且离奇的想象,突显了对于感知模拟的技术探索的未来展望。自科技的角度而言,正式进入虚拟现实(VR)领域可追溯至1956年左右,当时Morton Heiling创造了世界上首个虚拟现实设备,即VR原型机。该设备名为“Sensorama”,融合了声音和视觉的基本元素,并进一步结合了3D屏幕、立体声、气味以及震动体感等技术,模拟人类的各种感官体验。参与者只需坐在类似游戏主机的大型机台椅上,并将头部靠近设备的内部,即可沉浸式地体验虚拟环境。真正标志着虚拟现实装置的出现是在1965年,由美国的Ivan Sutherland及其实验室的学生共同提出了头戴式显示器(Head-mounted display),他将其视为“终极显示器”。1969年,Sutherland发明了一种名为“达摩克斯之剑”的实体设备,通过该装置,用户能够窥视电脑程序所构建的虚拟世界,因而Sutherland首次提出了“虚拟世界”的概念。
迄今为止,虚拟性概念的更新已呈现多样化趋势,涵盖了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扩展现实(XR),以及最新引入的远程感知艺术(Telematic Art)。这些概念皆通过一种虚拟性手段,将图像跨越历史与空间的限制,呈现于我们眼前,以此突破时间与地域的束缚。
邱教授提及在其访学期间于日本所见,东京的NHK在浅草寺展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增强现实(AR)项目。该项目涵盖整条街道,旨在通过AR技术呈现浅草寺历史的画面。NHK团队收集了大量浅草寺前方历史悠久的照片,并将其整合至一款移动应用程序中。参与者下载该应用后,便可将自身虚拟置入历史场景中,体验与浅草寺历史相呼应的虚拟合成体验。此一项目一经NHK电台公之于众,立即吸引了大量民众前往浅草寺,参与并体验AR装置。这一举措使得人们得以超越百年的历史藩篱,将自身纳入这一历史存在的概念之中。说到虚拟现实(VR), 艺术家陶亚伦以机械动力为手段,推进参与者在虚拟影像世界中的体验。这一过程使得参与者感知到身体受到持续推动的力量,从而实现身体感知与影像前进速度的同步状态。更重要的一种突显重要性的沉浸式虚拟状态,实际上是源自近年来由诸如TeamLab以及法国的Cultural Spaces公司等实体所创新的投影技术(Projection Mapping)所带来的一种沉浸式体验。这些体验所呈现的影像,本质上皆为虚拟图像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从历史的快速进程中,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当代艺术正在经历的转变,其中包括互动性、沉浸性以及对信息密度的持续强调,这些因素使得美学体验和感官愉悦需要超越传统范畴。我们涉及的不仅是艺术的形而上特质或超脱精神,同时也涉及到艺术展示的空间,例如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些传统展示空间正在逐渐被配备了电脑屏幕和手动按钮的黑盒子游览空间所取代。艺术家Douglas Coupland曾深刻阐述,在虚拟艺术领域中,其装置不仅影响了人类的本能反应或称之为“爬虫脑”,而且也牵制了我们的额叶皮质和前庭系统。因此,一旦我们深入虚拟现实的世界,我们彻底融入其中,难以从中解脱以从事其他活动。我们成为虚拟现实的一部分,而虚拟现实也成为我们整体的一部分。
对于上述概括的概念,当代理论学家Hito Steyerl所抱持的悲观态度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在她的论述中将虚拟实境及360度全景影像所呈现的空间,视作通过环形镜头和球形物体定义的投影。她提出了“气泡视野” (Bubble Vision)这一全新的视觉范式,认为虚拟实境实际上象征着一种孤立的美学。这种体验将观者置于特定空间中,使其感知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中心,但却与外部世界隔绝,形成了诸多矛盾。尽管参与者被置于环境场景的中心,但其身体却似乎消失了。他们只能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视角参与,可能会在第三人称视角中看到自己的手部,但这种体验却是一种残缺和异化的状态。Steyerl认为,这种身体消失的状态具有深刻的恐怖意义。
在哲学论述中,邱志勇教授将其概括为一场关于唯心主义(Idealism)与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之间的辩论。唯心主义(Idealism)源自笛卡尔主义传统,乐观地认为数字科技所带来的全新感知是理性科学发展的极致,它能使我们的身体摆脱物质束缚,达到灵魂的永恒状态。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所谓的物质性逐渐消退,转变为无物质存在的数字运动,或者说是数字代理的状态。然而,在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的框架下,对新科技的能量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人类历史会被数字科技改写,因为这动摇了或冲击了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所奠定的真实基础。这种真实被视为凭眼见为实,必须有物质存在才能被信任。所谓的真实是通过感官刺激经验到的物体。而相反,数字科技产生的经验是一种完全虚拟的真实,缺乏物质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者之间存在极端的相互辩证过程。
那么“到底什么是虚拟?”,邱教授再次用三个故事将我们的视角带回到传统的哲学思想里。首先,论及华人世界中经典故事《庄周孟蝶》,其梦境场景提供了当代哲学探讨虚拟性的一个范例。这一梦境世界作为一个非电脑辅助的虚拟领域,对于探讨虚拟性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次,印度教中的哲学民间故事《那罗陀变身》(Narada’s transformation)深刻探讨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困境。故事中,那罗陀在其一生中扮演了多个化身,受到幻象与现实之间的困扰。此后,好莱坞动画影集《Rick and Morty》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现代版本的动画故事Roy: A Life Well Lived。第三个经典案例为西方世界中的柏拉图寓言《柏拉图的洞穴》。该寓言描述了一群人被囚禁在洞穴中,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并将这些影子误认为真实。柏拉图通过这一寓言暗示,那些能够从洞穴中走出、看到真实世界的人,象征着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成为唯一能够认知真理的人,他能够超越感官世界,理解理念的本质,而不为表面现象所蒙蔽。
以上三则故事所呈现的情境,探讨了哲学作为对知识(即我们对世界认知的过程——比如庄子如何分辨梦境与现实)、现实(即世界本体的本质——比如罗陀的化身究竟是真实还是幻象)、价值观(即善恶的辨析——比如柏拉图洞穴中的美好生活)的研究。在当代背景下,这些故事中的梦境、化身、影子被转化为一种虚拟场景,进而引发了关于个体是否能辨别自身存在于虚拟世界之中、虚拟世界的本质是真实还是虚幻、以及个体是否能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美好生活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了当代虚拟与实际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引出了对“现实”本质的质疑,“到底什么是现实?”。
在电影《The Matrix》中Morpheus给Neo解释到“What is real? How do you define real? If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 you can feel, what you can smell, what you can taste and see, then “real” is simply electrical signals interpreted by your brain.”如果我们将现实定义为大脑所解读的电子信号,那么虚拟实境所呈现的影像、声音等也不过是作用在大脑中的电子信号而已。因此,虚拟实境可以被视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呈现方式,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则可能更多是基于我们的感知和认知。在讨论虚拟现实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如何利用技术让参与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到虚拟环境,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所谓的虚拟。
1911年Harry Grant Dart在Life Magazine中的插画“We’ll all be happy then”,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展现出20世纪初期人们对媒体和科技的想象。它描绘了一个未来场景,其中所有的影、视、音和设备都集中在一起,而人则置身于其中。这也预示了虚拟艺术和虚拟现实的概念,其中声音、影像和体感被整合到一个系统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设备变得越来越小和整合,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感官输入与输出体验。VR技术利用电脑模拟和同步用户的行为,通过头戴设备和手持感应器提供图像和声音的反馈。当用户戴上头戴设备时,电脑根据其动作实时生成相应的图像和声音,使用户能够立即看到360度的图像。因此,用户必须即时模拟并反应出这些图像和声音,以便能够体验到立即的虚拟环境。
到了1990年代末期,Michael Heim提出了一个介于唯心主义(Idealism)与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之间的观点,被称为虚拟实在论(Virtual Realism)。即虚拟实境相对于真实的物质并没有真实的实体,是人类文明跟世界的一种新的模式。这一范式的出现迫使我们必须在文化层面进行改变,积极地接受虚拟实在的技术,并重新审视人类文明中的象征元素。Michael Heim指出这一新装置实际上导致了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shift),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正在不断地转向虚拟化的过程。这种转向的过程在本质上重新引领我们认识一个新世界的概念。
另外一位德国学者Oliver Grau在《Virtual Art》一书中,用历史的观点审视虚拟实境的发展。他将其追溯到巴洛克时代的全景画(panorama),从绘画中的错觉(illusion)到当代的沉浸体验(immersion),强调观众感知在虚拟影像世界中的同等重要性,与影像本身具有同等地位。
美国新学院媒体研究学院的教授Christiane Paul指出,对于数位艺术或新媒体科技所带来的挑战,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其所谓的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这种非物质性主要表现在软件、系统和网络等计算机基础形式的展现中。软件是可见但不可触摸的,系统在视觉背后运作,而电脑网络连接则隐藏在显示界面之后。这些技术的后端在物质层面上是不可见的。传统的哲学家和理论学家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非物质的,是一种虚拟的状态,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们。
但是美国科学家Jaron Lanier在《Dawn of the New Everything》书中给VR的定义是,VR的根本使用是找到一种新语言,或一种新的沟通面向,以超越我们所知的语言。这也带来了我们讨论的焦点,新科技所带来的隔离性和唯我论特质。戴上VR设备后,个人被隔离,仿佛灵魂被掏空。在VR世界中,外部观察者看不到个人的行为,只能通过屏幕投影来了解。如果将VR视为一种艺术媒体,它可能受到唯我论特质的限制,即使用者被孤立,无法与外界互动。尽管存在团体观影经验,但在VR世界中,仍然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体验。
这种所谓的非物质性迷思(the myth of immateriality),一直存在于虚拟现实的讨论中。电脑计算的本质和编码的运作方式都是未知的。虚拟现实是短暂的(ephemeral),类似表演艺术,我们可以观赏但不会永久存在。它是一种非体现的(disembodied)、非永久(impermanent)、非现地的(non-locative)方式呈现。
1985年,Jean-François Lyotard在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举办的展览“非物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将虚拟视为一种新的物质文明,一种实体与物质的新条件。他的问题是,在经历巨大科技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新物质文明的出现可能性。
在William Ford Gibson的小说《Neuromancer》中,由装置所幻化出来的影像可以被转变由一种形式、影像和感官所构成的经验。他把它称之为是计算质(computronium),这些东西现在都一一的被科学所实现(actualization)。书中描述到,意识被分裂并呈现出球状的视觉,类似于现在所谓的360度全景投影的概念。一切都可以被技术化,比如沙滩上的沙粒、黄色包内的物品、甚至拉链上的磁孔,都可以用数字来计算。这体现了虚拟现实中的非物质概念,基本上是由0和1这两种运算的最基本的位元,即比特或字节构成的。所以,虚拟艺术是存在于一种介于媒介特殊性与非物质表演性间的吊诡连续体之中。
Christiane Paul进一步指出,艺术实践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物质状态。重新定义数字技术的冲击、特性和结构,它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新的多样化的物质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扩展的媒介概念,可以被扩展。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本质,就能够真正理解新媒体的特性所在。什么是新物质呢?新物质指的是在数字时代存在的一种物性(objecthood),与传统物质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物性涉及到网络数字科技如何嵌入(embed)、处理(process)和回应(reflect back)人类与环境的数据(data),并通过形式展现出来,突显了数字时代的本质。这种本质实际上是编码的物质性,以及数字处理过程如何重新审视世界的一种方法。
这样的一个观念论述与一些论点概念不谋而合:
意大利的创作者Alessandro Ludovico在谈的后数位(Post-Digital),强调了数字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数字原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再需要解释什么是数字,因为数字科技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生活,包括数字设备、界面和感知体验。这种后数位的概念反映了一种新的物质文明,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Marisa Olsen讨论了后网路(Post-Internet)的概念,强调了数字连通性的重要性。Olsen指出,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人们逐渐进入了一种24小时在线的状态,即使关闭电脑或手机,数字化的个人形象和社交互动仍在持续。在后网路时代,人们基本上是在持续在线状态下进行创作,可以随意地拼贴、重新组装、下载、转换和挪用各种数字内容。这导致影像创作变成了一种无底片、无镜头的新形式,完全基于数字网络,重新定义了创作的可能性。
Bernard Stiegle论述了超物质化(Hypermaterilization)的概念,强调了数位科技和生物科技的结合。Stiegler指出,在数位时代,这两种技术将所有物质融合在一起,人类开始进入一个后种系的生态,即人与技术的结合体。这种物质文明的进化使得生物科技和数位科技不再仅限于人体外,而是进入到人体内部,包括医疗科技的创新,通过维持器官的运作,帮助人类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与机器、生物与机械、自然与技术相互融合的物质文明的时代。
James Bridle提出了新美学(New Aesthetic)的概念,认为在数位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美学。传统美学建立在一套固定的知识体系上,将其作为评价外部世界的标准。然而,在数位时代,新美学要求我们重新回归到本质层面去探讨美学。数位时代的美学重新思考了数字的本质,将0和1的运算方式重新诠释为一种新的美学经验。这种美学经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影像形式,而是包括底片、照片、胶卷等形式,同时考虑数字存在的物质性和逻辑性。数位时代的新美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美感经验,重新定义了美的标准和评价方式。
邱教授花了一些时间时间来与我们探讨这些论点,主要原因是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和观念,重新审视了数位时代中物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新观念。新物质性的主要特征在于数位科技与各种不同物质之间的交融,这种交融改变了我们与这些物质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主体性,以强调主体性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反思和互动。其假设了一种高度反思性的状态,将数位科技的冲击视为一种在不同科技和物质之间交流融合的状态。它重新定义了我们与这些物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的可能性。可以说,新物质性不仅突显了当代观看的状态,还告诉了我们如何通过数位科技来观察世界,同时突显了数位科技发明媒体和媒材的能力。它的后端是编码和计算创造力,而前端则展示了传统的视觉、文明和文化背景,使我们能够真正理解通过电脑运算逻辑所呈现和传达的内容和意义。
Rodrigo Guzman Serrano通过扩张的非物质性(Expanded Immateriality)概念,以辩证的方法告诉我们重新审视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看法的重要性。他认为媒体艺术的媒介性应该被理解为特定感性场域中的一种现象,即在特定的空间和情境中讨论和观看艺术。这种媒介性可以作为物质或技术的基础,也可以转化为观念、概念或论述的基础。换言之,它既可以是硬体的实体,也可以是抽象的观念,甚至可以是软体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关于场域和空间性的讨论,以及感知环境的概念。
整个讲座分享过程中,邱教授重新用一种新物质主义的概念,去谈物到底应该是什么,并且讨论新的媒体科技的一个延伸跟发展。主要讨论了影像、科技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过程,重点包括:
- 在影像与科技之间(图像),探讨了技术性图像的生成与变化。
数位的图像代表了一种持续处于当下、不断生成的状态。这种图像基于时间的概念,具有接续性和生成性的能力。它不仅完全展现在空间或时间中,而且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语法在荧幕上实时呈现出视觉化的过程。与静态文字性表现相比,数位图像通过算法在冰冷的数据和语法中生成具有情感、色彩、笔触和风格的影像。在生成过程中,这些算法通过数学方式创造出类似米罗、康丁斯基等抽象化风格的图像。在虚拟现实世界或数位空间中,图像是不断生成的,展现了一种持续变化和创新的概念。
- 在受众与科技之间(介面),重点在于介面科技的物质性和文化意涵的迭代发展。
介面是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双向薄膜,基于关系的形式。在介面的后端,存在着一系列电脑程式语法的运作,这些运作通常是人们难以理解的。然而,在介面的前端,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性的呈现,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示给我们可以理解的内容。因此,介面应被视为一个分离和聚合、限制和开启、归线和实现、排除和涵掘的双向过程。
- 在影像与受众之间(感知),涉及了沉浸感知历史性变迁的话题。
感知层面体现了一种共感连续的美学,即观众在虚拟现实世界中必须能够建立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这种体验是通过一系列成熟的实作所构建的虚拟世界来实现的。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观众通过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感官经验来建立完整的感知体验。在英文中,这被称为“Think Aesthetics”或者“Synthetic Aesthetics”,强调了一种连贯且共鸣的状态。
邱教授一直强调数位媒体,包括电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以及更先进的扩展现实(XR)概念,本质上都是软件。它们的数位形态(digital appearance)是通过计算机的模拟计算产生的,是一种综整的(synthetic)转换过程。这个过程涉及生成不同影像呈现方式的方法,综合声音和影像,以及创造虚拟空间,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这些媒体在影像空间、界面和感知之间建立了连接,使体验者与之互动。然而,它们的背后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不稳定的、无限程式化的过程。
可以说VR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艺术的感知和观感。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探讨我们与VR、这种媒体和界面之间的关系。重新回到“虚拟”这个名词,Marie-Laure Ryan将其追溯到拉丁文,其意思是具有潜力或力量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论述相关。虚拟实境不完全是幻觉或虚构的,虚拟实境中的事件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人们在虚拟现实中互动的对象具有实在性,不是真实的哲学对立面,而是一种存在的状态。现代概念中的模拟现实主义(Simulation Realism)和虚拟数位主义(Virtual digitalism)也表明,虚拟世界中的物体实际上是以位元和字节的形式存在的。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触摸位元或字节,但科学实验证明它们具有微小但存在的重量。虚拟世界的实体虽然轻微,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在虚拟世界中的互动也可能是一种美好的体验,人们也可以享受有意义的生活。
在讨论不同艺术时代和媒介的物质性时,我们也看到了物质的演变。从绘画时代的颜料,到摄影时代的化学物质和光学技术,再到以时间为基础的媒介如数位媒体,物质性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当代,AI和生成艺术重新定义了媒介,将资料库的概念解放为一种指令,并通过算法和机器学习来产生文字、图像和动态影像等作品,甚至包括数化分身,这些都成为可能。
因此,在数位时代特别是以VR为例,我们要重新认识虚拟影像和数位讯号的物质性存在。这种物质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存在,而是一种基于数位的虚拟概念。最后,邱教授提醒到,我们需要采用新的知识体系来理解这些内容,而不是用传统的类比思维来思考“虚拟要如何构建一个新真实的知识框架?”等问题。
互动与思考
在数位世界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人类感官无法感知毫秒级的时间差或几乎无法辨识的重量。例如,我们很难感受到一个bit的重量,常常用“无感”来形容。尽管邱教授今天分享的PPT包含大量数据和生成的图像,总共有3.9G的数据量,但对于听众来说,与12MB或30MB的文件相比,我们可能并没有明显的感受。然而,当我们的电脑无法运转或硬盘容量不足时,我们又会感受到这些数据的庞大。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来描述和测量这些数据,但我们的感知能力,目前仍然无法真正理解或感受到其巨大的量级。
不管是学者或是一般大众,对于虚拟现实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对视觉影像的依赖,但是否有可能在VR中存在没有任何内容的作品?这个问题也引发了对我们是否过于依赖图像和文字描述来激发感官的思考。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点,并批判地思考数字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数字化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们应该以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它,同时适应并利用这种新的世界。在讨论VR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AR)等技术。这些技术的背后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作用主体,即所谓的agent,它不仅仅是AI的概念,也是一种生成的过程。在未来我们仍需深入思考这些技术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如何与之互动。
在探讨数位艺术对人们世界观和身份认同的影响时,我们涉及到了另一个庞大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关于个体身体主体性的建构,是通过自身对自我身体的认知,还是通过外部环境的反馈来塑造。社会学和其他学科有许多相关的理论和讨论,但在当代数位世界中,我们更多地是通过展示自己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的主体性。传统上,我们认为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圆,另外一个圆是虚拟的世界,即虚拟的世界不在真实的世界里面。邱教授认为它们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虚拟世界是真实世界的一种表现方式,数位科技作为界面,让虚拟与现实相交融。在探索这些世界的交融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引用一些幽默的说法,比如说AR让我们看到“鬼”,VR带我们“观落阴”,而XR则让我们继续看到“鬼”。这些玩笑背后也反映了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的感知和体验。
在20世纪初期,一位女性主义艺术家在文章中写到:“When I get online. Can I leave my body behind?” 。这个问题强调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是相互连接的,而不是相互隔离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每个人对于如何认识自己都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人们更多地沉浸在一种自我展示、自恋的文化现象中,例如自拍文化。
每个人对于虚拟世界的体验是独特的,就像戴上VR头显体验时可能会出现3D晕一样。这种现象表明了人们的身体感官和影像速度之间的不同步可能导致的晕眩感。同样地,人们对于VR虚拟世界的认同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Douglas Coupland来说,他在使用VR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心理落差。一方面,他体验完虚拟世界后回到现实世界时,感受到了现实感的丧失,这给他带来了心理上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主体性的断裂,不确定虚拟世界中的替身是否还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Coupland将这种状态描述为“后VR的忧伤”,强调了现实感和主体感之间的落差。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暗示着,我们对于虚拟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仍然面临着挑战,后续可以进行深入探讨并寻求解决方案。